鲁东大学文学院 黄修志、郑嘉琳
《“再造藩邦”之师:万历抗倭援朝明军将士群体研究》,孙卫国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344页,9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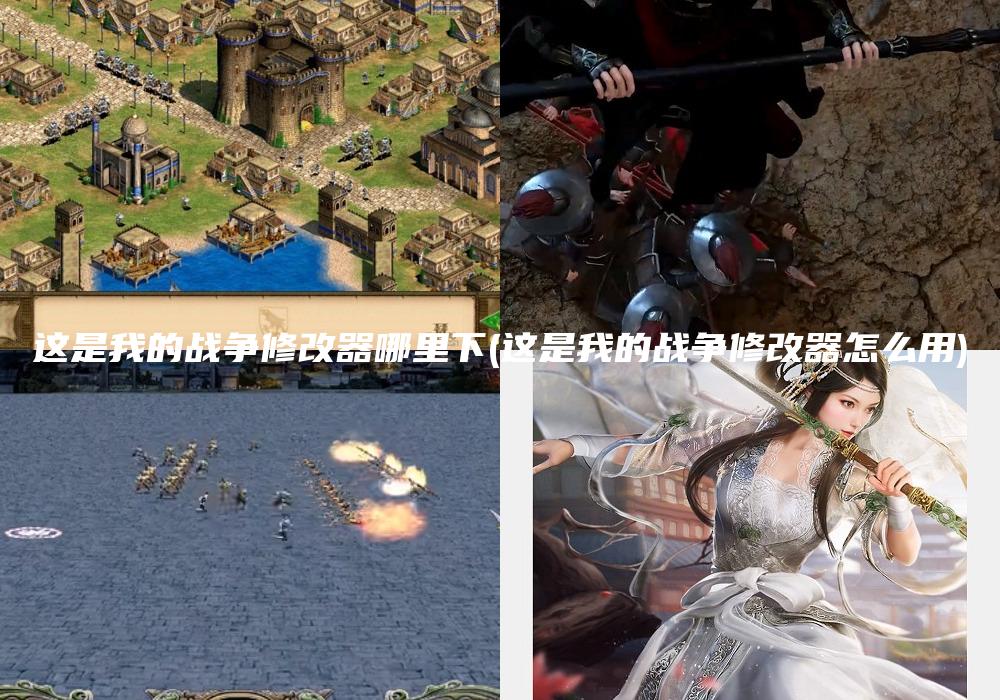
1592年适逢神宗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朝鲜在几近亡国之际向明廷请兵支援,明廷调遣南北精锐部队赶赴朝鲜战场,开启了长达七年的抗倭援朝战争。关于这场震荡东亚、影响深远的国际战争,中、韩、日及欧美学界虽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却在不少问题上言人人殊,尤其是对明军将士群体的角色定位和重要战争的成败得失更是聚讼纷纭。可见四百多年来,传世文献和学界研究为这场战争和明军将士群体涂上了“历史的严妆”。在史家孙卫国看来,关于此群体的历史书写和战争记忆主要经历了三层遮蔽。
一是明朝内部的党同伐异,此为第一层遮蔽。从出征开始,明军将士就处于朋党之争、文武之争、战和之争、南北之争、宗藩矛盾中,影响了《明神宗实录》等明朝史籍的书写,导致明代第一手资料从一开始就在书写心术和思想观念上出现了偏颇。二是明清易代后的政治偏见,此为第二层遮蔽。由于不少援朝将士也在辽东战场与后金作战,导致清代官私史家有意贬低明军将士,而且,杨海英也指出,自清修《明史》开始,便断言明亡于万历,“出自塑造清朝统治正统的需要,有意无意将万历皇帝和他的大臣都置于负面评价之中”。三是近代以来韩日两国的民族主义史学,此为第三层遮蔽。无论是韩国不少学者为凸显本民族的主体性和自尊性,还是如韩东育所言,日本自1592至1945年形成了“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两国学界都有肆意丑化明军将士、贬低无视明军战绩的显著倾向。
在此背景下,孙卫国继《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嬗变(1627-1910)》两部典范论著后,又推出第三部力作《“再造藩邦”之师:万历抗倭援朝明军将士群体研究》,试图反驳韩日学界在万历抗倭援朝战争研究方面的民族主义倾向,“在东亚视野下重新反思明清史籍的成书过程”,指明“政治干扰与王朝更替造成明清史籍记载失真”。罗新倡议历史研究者应“走出民族主义史学”,那么孙卫国是如何以公心为明军将士群体“正名”和“辩诬”的?明军将士在诸多关键战役中的具体表现如何?关于明军将士的种种历史书写又是如何在战争前后被塑造的?若细细披览该书,自然心有所得。
其二,分析人物心态,回归历史语境。孙卫国笔下的明军将士有着鲜活复杂的性格,既受制于时代环境,又影响战争走向。芭芭拉·塔奇曼在《历史的技艺》一书中说:“凡人——你、我、拿破仑——不敷为科学的因素,结合了性格、环境和历史的情景,任何人都是无数变量的集合,无法复制。”个案可以帮助细化这些“变量集合”在其所处历史场景中的作用,使战争研究发生个人转向,以微观分析带动宏观叙述。以往研究中,明军将士角色大多要么较为程式化,要么因选取较多而丧失个体独特性。孙卫国不仅重视明军将士的沙场表现,还考察个人性格心态、仕途履历、人情关系对战时处事之影响,且通过朝鲜君臣的视角表现出来。如李如松在碧蹄馆之役中伤心于折损多数亲兵家丁,成为之后倾向封贡的重要因素。朝鲜对石星态度极其复杂,一方面不满其修改表文,偏听偏信,行事莽撞,另一方面也清楚石星“自始至终,为我国经营百度”,对其因“愚戆”和“无知”而瘐死狱中感愧不已。朝鲜国王宣祖对经略宋应昌印象很差,但赞赏杨镐尽心战事,行事严密迅速。宋应昌晚年处境艰难,撰写《经略复国要编》,扭曲史实,意在自我辩解,引起朝鲜君臣不满。历史终究是无数个形态各异的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战争这种激变时刻,个人的特殊性不免影响历史的走向。
《抗倭图》卷(局部),明。
关于明朝抗倭援朝战争与朝鲜对其“再造藩邦”的感恩意识,韩国某代表性学者曾分析朝鲜王室在战争过程中为缓解统治权威的危机开始强化对明感恩意识,他强调明朝的参战是为确保本国安全的自卫性措施且在朝鲜造成了扰民等问题。这基本可以折射出不少韩国学者的研究旨趣,然而,同为韩国学者的桂胜范对此类研究观点提出批评,认为“这些其实都是与整体战况没有直接关联的附带性问题,原因在于:第一,完全不计较本国利害关系便对外国派兵的愚蠢国家在历史上几乎是找不到的;第二,在对日军不具备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明朝想通过和谈来结束战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三,明军应朝鲜之求而参战,朝鲜提供军粮也是理所当然;第四,明军带来的民弊并不能抹杀明军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
其实,若我们细察该书,孙卫国对韩国此类研究观点也有回应。该书第二章中,朝鲜请兵陈奏使郑昆寿在给兵部尚书石星的呈文中说得极其明白,明廷必须救援朝鲜不仅是基于“字小之仁”的道德义务,也是为了保卫“中国疆场之安危”,可见明军基于唇亡齿寒而参战是战争开始就有的两国共识。关于这一点,陈尚胜认为明朝参战是由“字小”立场和国家利益共同决定,刘晓东认为明朝基于“恤远字小”的伦理义务决定出兵援朝。这就提醒我们,除了现代人可以理解的国家利益外,明朝参战也源于古代中国深怀“事大字小”的精神信念和道德伦理。在军粮问题上,孙卫国指出,战争之初,朝鲜大批粮草被日军焚毁或被饥民抢夺,此后的主要后勤保障都需要明朝提供,既供应粮草又拨付白银,但“朝鲜国力过弱,几乎难以完成从鸭绿江边运送物资到前线的任务”,待丁酉再援时,明朝通过海运勉强保障了物资供应,既提供给明军,也供给朝鲜君臣和百姓。而在扰民问题上,无论是明将还是明臣都察觉到明军在朝鲜造成了一定的扰民问题,故而也努力严肃军纪,制止扰民。另外,如果说朝鲜感恩明朝和强调明军功绩只是朝鲜为解决内部统治危机而刻意制造出来的,那么朝鲜在战后以明军南兵为榜样,参照戚继光《纪效新书》而彻底改造朝鲜军队制度就难以解释了。毕竟,文化仪式可以塑造,但最重要的国防力量根据别国军队而进行彻底改造就没那么简单了。
可以看到,围绕抗倭援朝的战争记忆,四百多年来经历了各种历史书写,如今也在继续。人们纷纷对一个历史事件进行各种解读,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当下时局有所关切,因此,历史书写具有非线性建构的特点,容易受到不同时代的思想氛围或意识形态的“侵袭”或“置喙”,继而影响人们对当下政治或未来战争的态度。就不同国家的研究来说,不少韩国、日本学者缺乏历史大局观,这也影响到西方学者对明军的定位,如该书附录对塞缪尔·霍利《壬辰战争》所撰书评所示,孙卫国所批判的,是带有诱导性、歪曲战争记忆、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历史书写。就中国学界来说,广大读者尤其是业余历史爱好者对这场战争的讨论兴致勃勃,朱尔旦《万历朝鲜战争全史》值得学界重视,但目前仍缺乏一系列论证严谨又文笔晓畅的著作增进民众对这场战争的认识,这无疑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在《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一书中说:“专业历史学家不应该轻易将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拱手让于他人。我们有必要尽最大努力来提高公众对历史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认识。我们还必须要驳斥那些公共领域中片面的甚至错误的历史叙述。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等于说我们在放任领导人和意见领袖利用历史为一些错误的论调背书,为那些糟糕愚蠢的政策辩护。”应该说,孙卫国《“再造藩邦”之师》已为学界树立了标杆和榜样,如今,一批年轻学者也在此领域崭露头角,相信他们必会迎头赶上,不断超越,走向新的峰顶。






